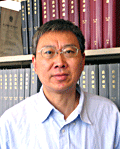
徐贲
徐贲,爱思想网学术委员。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,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。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-Intellectuals(1992)、Disenchanted Democracy(1999)、《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》(1996)、《文化批评往何处去》(1998)、《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》、《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》(2008)等。
微信扫码订阅 推送实时更新
论文
- AI与人类自毁的文学反思
- 公共说理如何避免“越说越僵”
- 逆境忧患与抑郁现实主义
- 苏联儿童:我们最幸福
- 平反、道歉和现代道德政治
- 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
- “我们”是谁?——论文化批评中的共同体身份认同问题
- 纳粹德国的党国主义教育
- 毛主席赠芒果的一种解读
- 普遍人权的四个价值支柱
- 话说“政协”
- 中国的“新极权主义”及其末世景象
- 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——马基雅维里的启示
- 宽容、权利和法制
- 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
- 当今中国文化讨论需要关注的伦理话语
- 文化讨论和公民意识
- 从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到知识公民政治
- 什么是中国的“后新时期”和“后现代”?
- 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
- 阿伦特论“平庸的邪恶”
- 大国崛起和“中国认同”的普遍价值问题
- 秩序和道义:哈贝玛斯的国际人权观
- 公共话语的逻辑与说理:《中国不高兴》的教训
- 公民教育·民主政治·爱国主义
- 战后德国宪政与民主政治文化——哈贝马斯的宪政观
-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写作
- 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东欧学习?
- 苏格拉底对话中的“公民服从”:思想者的政治技艺
- 指点改革迷津的智者:列奥·施特劳斯的《论暴政》
- 媒介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字和图象
- 红潮往事: 告别“党人革命”
- “记忆窃贼”和见证叙事的公共意义
- 见证极权统治下的日常生活
- 奉命干脏活的人们
- 诗性人类学的群众理论:兼及卡内提和阿多诺关于群众问题的对谈
- 扮装技艺、表演政治和“敢曝(camp)美学”
- 毛主席赠芒果的一种解读:重建中国社会的礼物关系
- 阿伦特公民观述评
- 以民族解放的名义:反殖民的法农和暴力的法农
- 马克思会怎么说?暴力革命中的隐秘群众理论
- 公共生活和“说故事”:文学的阿伦特
- 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: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
-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:“捷克现象学”回顾
- 抗恶的防线:极权专制下的个人“思想”和“判断”
- 和谐、记忆和现代人际伦理
- 文革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
- 革命知识分子和“正义”暴力
- “文革”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
- 保护弱者,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
- 公共视野中的“革命”和“政治自由”
- “需要”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
- 中国不需要这样的“政治”和“主权者决断” :“施米特热”和国家主义
- 政治神学的教训:失节的施米特
- 施米特现象和右翼批判理论
- 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: 解读三种文革记忆
- 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 ——“超级女声”的公众意义
- 后现代价值观和文化相对论
- 以骄傲的反抗积极生活:阿伦特和存在主义
- “公民新闻”和新闻的公共政治意义
- 全球化、博物馆和民族国家
-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:哈贝玛斯的宪政观
- 干净的手和肮脏的手:知识分子政治和暴力
-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
- 公共生活和群体认同
- 公共真实中的社会和谐:和谐社会和公民社会
-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和福楼拜研究
- 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
- 学术规范的社会理想:从“新国学”的价值观谈起
- 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:阿伦特的公民观
- 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治
- 晚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
- 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存在主义
- 承诺、信任和制度秩序:当今中国的信任匮缺和转化
- 重提“政治文化”
- 能动观众和大众文化公众空间
- 当今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
- 大众传媒时代的闲言八卦:从杨振宁和翁帆婚恋看当今“新闻”
-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
- 民主社群和公民教育:五十年后说杜威
- 教育场域和民主学堂
-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:社会正义在中国
-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
- 正义和社会之善
- 公民新闻、公众和公共政治
- 从公共生活看全球化和公民群体认同
-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
- 自由市场和公民政治: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
- 民族主义、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
- 弱者的抵抗
- 平反、道歉和国家非正义
- 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
- 战争伦理和群体认同分歧
- 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
- 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
- 从宪法的形式性看中国宪政问题
- 后极权和东欧知识分子政治
- 国人之过和公民责任:也谈文革忏悔
- 理性、伦理和公民政治: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
- “密友资本主义”背景下的社会冲突: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
- 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
- 平庸的邪恶和个人在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
时评
- 数码时代的大学知识
- 中国社会为何普遍粗鄙化?
- 情绪联网时代的犬儒主义
- 为什么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悔罪上差异这么大?
- 日本为什么不悔罪
- 脏话有悖个人荣誉
- 毕福剑和他的玩笑:假面社会里的犬儒主义
- 当今中国社会的颓废与犬儒
- 说理要避免“动机指责”
- 官员腐败与饕餮之罪
- 涉“色”腐败为何令人恶心
- 你的“幽默”违背常识
- 陈光标是在高调消费不是做慈善
- 慰安妇塑像的法律与人道之争
- “整容”的政治与伦理
- 当“你懂的”成为公共语言
- 扎进日常语言的带钩渔叉
- 雾霾里的乐观和犬儒
- 宋彬彬的“错”和“罪”
- “讹人大妈”与“辱华洋人”
- 法治需要"敬畏"法律吗?
- 言论的理由
- 公共说理如何避免“越说越僵”
- 钱袋上的对抗——美国“政府关闭”的历史剧
- 政府关门和党争之害
- 什么是“心魔”
- “谣言”有那么可怕吗
- “红卫兵”道歉是一种怎样的良心行为
- 勿轻信,勿偏执
- 中国气功的“人群效应”
- 当今中国情非得已的“在商言商”
- 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
- 告别文学研究的“室内游戏”
- 管管闲事多多嘴
- “中国梦”与“美国梦”的差别
- 公共话语危机中的“公知” 背运
- 选民对政客的“审慎信任”
- 宪政法治中的“人民领袖”
- “道德正确”的胡说八道
- 不管改革有多难,都心怀期待
- 政治改革仅有梦想是不够的
- 说真话的前提是,先让人能说话
- 宪政的根本作用是防止暴政
- 中国为何普遍粗鄙化
- 改良不是清除八股官话的根本出路
- “改良八股官腔”必然会失败
- 宪政需要怎样的制度守护
- 美国的竞选与金钱
- “选民访谈”与“幸福调查”
- 人微言轻的选票是民主的最强力量
- 金钱不是美国选民的唯一“自我利益”
- 让公民交谈代替群众呐喊
- 中国“共识”需要怎样的理性话语
- 美国人的选举投票和“入党”
- NBA使汉语“不纯洁”了吗?
- 选民不信任政客是美国政治的常态
- 民众对政府的“行政保密”拥有怎样的知情权
- 中国人会“说话”但不会说“理”
- 屁话比谎话危害更大!
- 中国人对色情太敏感
- 中国人拜偶像的心灵危机
- 什么是《知青》“激情岁月”的激情?
- 社会需要自由、理性的文科
- 文科的厄运与责任
- 电视剧《知青》带来什么样的记忆?
- 作家集体抄书是耻辱,不是荣誉
- 大学之门不应对失足青年关闭
- 有利可图的“有机知识分子”
- 精英如何介入大众文化
- 慎谈美德也许正是一种美德
- 把人民当傻子的“开明君主”和“伟大领袖”
- 政体改革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
- 优秀的政体必须追求优秀的价值
- “充分公民”是衡量政体优劣的标准
- 政体是制度与公民文化的结合
- 公共话语中的“纳粹法则”
- “好人综合症”是一种心理疾病
- 美国的“理性集会”
- “政治好人”雷锋
- 外来价值有那么可怕吗?
- 如何对世界说“这就是中国”
- 美国大选中的“公正”价值
- 美国大选中有“两条路线斗争”吗
- 软实力和价值观
- 软实力不是一个新问题
- 没有信仰的政治人物令人害怕
- 2011年“抗议”中的“人多势众”
- 网络说理要变温和
- 再谈“微博”与“说理”
-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,不是攥紧的拳头
- 微博是好的说理形式吗?
- 少女援交与中国人的幸福
- “谴责”和“声讨”不是说理
- 公共言论中的“骂”
- 市检察长之争与司法民主
- “成人化”让儿童失去羞耻感
- 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
- 在自发的民众运动中表达诉求
- 任何人都不该因贫困而受“羞辱”
- 美国五六年级小学生写自己的“看法”
- 美国的政府有权改变人民的决议吗
- 9.11十周年之际的“美国问题”
- 骆家辉的操守与美国的制度设计
- 官场腐败是一种怎样的传染病?
- 从不相信到犬儒社会
- 警句格言的引述问题
- 新闻发言人不是辩护律师
- 不要让“网骂”变成“破口大骂”
- 对美国“党性”政治的不信任与降级
- 追思逝者是一种公民教养
- 国家不是公司,政府不是老板
- 美国最高法院如何看待“言论自由”
- 法律要保护“少数人”的权利
- 假如药家鑫案发生在美国
- 尚未成为过去的美国内战
- 对公民,我们缺少“不公开”的意识
- “唱红歌”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
- “农民工”人大代表的喜和忧
- 没有“市民权利”就没有城市
- 暴力征收与拦路打劫是同等恶行
- 民众的知情权到底有多大
- 干部赴美国“挂职”能学什么
- 从不伤害动物到尊重生命
- 美国独立选民的政治力量
- 维基解密与民意调查
- 他们为何怕“中期选举”
- 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道德
- 美国是怎样反“低俗”的
- 治理城市非得“严打”吗
- 过度运用口号和标语,妨碍公共理性
- 唐骏“学历门”和美国的“野鸡大学”
- 公共话语的伦理和价值观
- 学会讲道理:向美国基础教育学什么
- 教科书里的“文化政治”
- 人亡而政未息的人道正义
-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:暴力伤害和社会非正义
- 不要把说理当成了诡辩
- 美国人看不懂韩寒
- 美国“欺骗自己人”的政党宣传
- 党内包庇是党派政治的胎里病
- 医改法案和公民不服从
- 美国的党内包庇和两党对立
- 民主政治常用体育术语
- 为什么德国忏悔,日本和中国不忏悔?
- 极权统治下国民的四种“罪过”
- 个人忏悔不等于公民责任
- 马尔代夫给哥本哈根峰会带来的启示
- 什么是“和谐”?
- 吵架越成功 说理越失败
- 奥巴马政府为媒体“定性”的难题
- 美国的“上纲上线”宣传
- 奥巴马开学演说引发的争论
- 美国民众拒绝洗脑
- 在法律与民意之间的惩罚性正义
- 美国老师怎样“批评”学生
- 是什么力量在美国遏制腐败?
- 哈佛大学黑人教授被歧视对待了吗?
- 美国军人的荣誉观
- 如何与美国公务员打交道
- 60席不等于60票
-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
- 美国抗议税收游行发出什么信息
- 谁来主管美国的高等教育
- 反贪腐促成美国公务员的政治中立
- G20峰会点燃民粹之火
- “不高兴”先生要学会说理
- 军人宣誓和民主宪政的“武德”
- 总统和党主席
-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夫人
- 美国总统宣誓的真正约束来自什么
- 人的“公理”与“公设”
- 奥巴马就任总统宣的是什么誓
- 让孩子多问几个“为什么”
- 谁折腾和折腾谁
- 经济危机会引起美国动乱吗
- 吏治之弊 问责机制 社会信任
- 高等教育因何“高等”
- 美国大选中的公民社会
- 当今中国的性政治和思想解放
- 美国经验:公正的征税必须透明
- 善待底层民情
- 范美忠在美国会被开除吗?教师职责和公民权利
- 灾难和后灾难人性
- 替罪羊拯救不了我们的道德灵魂:谈范美忠事件
- 日常生活中的防震意识
- 敬畏自然 敬畏死亡
- 消费报道中的社会价值观
- “群体性事件”和暴力问题
- 如何才能对日本理直气壮?慰安妇雷桂英的见证
- 给陌生人的礼物
- 圣诞节的礼物
- 韩剧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道德习俗
随笔
- 人工智能时代的公民社会与民主,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?
- 愚蠢是怎样一种公共危害
- 道歉: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
- 关注“小真相”的知识分子
- 徐贲 :大学人文教育中的“科学”
- 美国人的“爱国主义”
- 统治与教育——从国民到公民
- 雾霾里的乐观和犬儒
- 选举政治的“负面倾向”
- 西方政治人物的“诚信”
- 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
- 无所作为的美国教育部
- “火大”的社会
- 如果朋友信任你
- 责任心VS同情心,哪个更重要?
- 公共语言中的“任性”
- 知识分子和政治犬儒主义
- “你懂的”是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
- 犬儒的生活智慧
- 该如何讨论“人治”
- 从势从利的犬儒式“势利”
- 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
- 电子短讯和邮件的“非礼”
- 美国的“通识教育”与“人文教育”
- 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
- 奥兹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
- “用脚后跟想”的犬儒主义
- 《朗读者》和纳粹罪恶的后代记忆
- “慈善”并非都是善事
- 父亲的“劳改日记”
- 自由言论塑造优秀的公民人格
- 德国纳粹体制下的人格分裂
- 我40年前的一位知青亡友
- 沾光和沾霉气
- 学做“精明的公民”
- 怀疑的时代需要自由的信仰
- 中国人的良心问题——不做“吃米饭的机器人”
- 刻印在人心上的律法
- 人文与言论
- 比“坏种”更恶劣的是“伪善”
- 两种不同的美国议员
- 共和法治的缔造者和初始时刻
- 无度时代的“贪婪”
- 异化比妖魔化更可怕!
- 群众激情宣泄的“羊咬兔子”
- 为弱者讲述的人权历史
- 公民说理,使真理获胜
- 提防“说得通”的胡说八道
- 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“利维坦”式的怪兽
-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
- 我们也曾经是迷惘的一代
- 穿上学位服的时刻
- 大众文化中的价值观
- 品格和美德教育必须去除恐惧
- 无权威无信仰时如何说理?
- 国民教育不能只用来培养顺民
- 他们为什么自杀
-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权利
- 美国的“政治大嘴巴”
- 创伤与怀旧并存的极权“后记忆”
- “复活”的斯大林
- “文革”的隐患在哪里
- 集体记忆的伦理和往事纪念的权利
- 奥巴马和鱼翅汤
- 波士顿学院的口述史事件
- 警惕“非人化”语言的敌意
- 虐待敌军尸体是什么样的战争罪行
- 统计数字的谎言
- 哈维尔的悲剧想象和公共政治
- 为什么我们会对谎言深信不疑
- 美国“富二代”的价值观
- 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
- 歪理为什么不觉得“歪”
- 解释宪法是法官的事,也是民众的事
- “制衡政治”和命运多舛的美国高铁
- 阅读和“精明的公民”
- “德意志问候”的趣闻
- 美国平等民权的重要一步
- 美国学生为什么不热衷坐办公室
-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末日预言
- 死刑监察官为何反对死刑
- 以眼还眼,以牙还牙
- 死刑和司法正义
- 让孩子慢慢长大
- 苏联人对斯大林的矛盾心理
- 中国的“身份低下者”们
- “人道”是一种社会价值
- 奥威尔:左翼的尽头在哪里
- 宪法和儿童抚养费
- “红歌”的三个主题和爱国主义
- 公共生活和公共议论
- 百年前的政府承诺该不该兑现
- 2010年岁末的死者追怀
- 《在傻子和英雄之间: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》序
- 罪、耻、惧与当今中国的道德困境(五之一)
- 崔卫平: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
- 隐瞒比犯错更不光彩
- 美国的不投票选民
- 美国选举中的劳工力量
- 我看美国“官二代”
- 美国初中课本里的核心价值
- 美国的言论自由和仇恨言论
- 公共生活中的“原罪”
- 纳税人的钱给政府用到哪里去了?
- 没有荣誉的民主政治并不优秀
- 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
- 制度和民情
- 人需要高尚价值的想象
- 美国司法审判中的常识判断
- 纳粹屠杀中的幸存者:为死者哀,为生者舞
- 美国的慈善和公民社会
- 教育工会反对美国教育大跃进
- 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
- 美国人不信任精英——人文教育的美国家园和外乡人列奥·施特劳斯
- 伤及无辜的“文化比较”
- 美国价值和美国身份政治
- 美国人为何关心大法官的任命
- “内部发行”和“墙”
- “需要”和“好生活”
- 修复公众形象的策略
- 普世价值和全球正义
- “数人头”的美国人口普查
- 画在希特勒书页上的人类抵抗
- “茶党”抗议和民粹政治
- 无神论者在美国担任公职的难处
- 东德的“党宣传”为何不能成功?
- 越是事实,越是诽谤?
- 有所不为的美国教育部
- 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林肯
- 《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: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》前言
- 美国学童说真话
- 美国青少年的政治读物
- 神不正义,人怎么办?
- 人为什么有利他行为
- 普世主义的价值和世界公民的人格: 二战后的雅斯贝尔斯
- 顺从的“觉悟者”:七十多年前的苏联青少年
- 在美国教伦理写作
- 拯救一棵树和保释一个人
- 大学荣誉的“守门人”在哪里?
- “死亡中有生的秘密”:读余虹
- 你还相信礼物吗? ——礼物六题
- 战后欧洲的文化使者:萨特、波芙娃和加缪在美国
- 正派社会和不羞辱
- 冷漠和不参与
读书
译作
访谈
本专栏经作者授权。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、出处并保持完整。纸媒转载请获得书面许可。

